一、“重读”的起点:由“人”出发还是由“事”出发?
赵树理的小说《邪不压正》1948年10月13日起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连载,马上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。1948年12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党自强的《〈邪不压正〉读后感》和韩北生的《读〈邪不压正〉后的感想与建议》两篇观点相互对立的文章。1949年1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又用了一个版的篇幅,发表了耿西的《漫谈〈邪不压正〉》、而东的《读〈邪不压正〉》、乔雨舟的《我也来插几句——关于〈邪不压正〉争论的我见》,王青的《关于〈邪不压正〉》一组文章展开讨论,同时还配发了《人民日报》编者的文章《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》。这篇文章指出,围绕《邪不压正》这篇小说“论争的重点,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,因而也牵涉到对农村阶级关系、对农村党的领导、对几年来党的农村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实施……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分歧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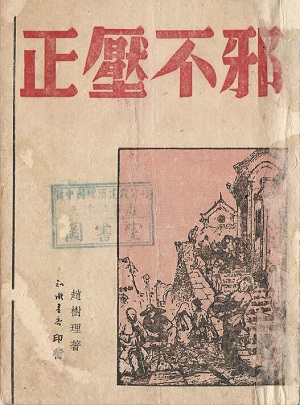
具体来看这场讨论,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止于“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”。党自强认为《邪不压正》“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,因此,纸上的软英是脱离现实的软英,纸上的封建地主是脱离现实的封建地主,于是看了这篇小说就好像看了一篇《今古奇观》差不多,对读者的教育意义不够大”。批评的焦点固然集中在“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”,但也隐含着将《邪不压正》理解为与《小二黑结婚》有着某种类似的、描写“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及其波折”的小说。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,他认为赵树理这部作品在“人物塑造”上存在着较大的失误:“小宝应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,应该是有骨气的。软英应是由希望、斗争、动摇、犹豫以致坚定。坚定的思想应该必须是在党的直接或间接教育培养下产生出来的。” 不过,另一位评论者耿西“不同意党自强同志那种结论。那个结论好像是从几个固定的框子里推断出来的,并没有切合实际的分析”,而且他与党自强的分歧还在于“赵树理这个作品不是写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,而是通过这个故事在写我们党的土改政策。特别是在写一个支部在土改中怎样把党对中农的政策执行错了,而又把它改正过来。这篇小说便是在这种波动中发生在一个农家的故事。这正是我们在土改运动的某个侧面和缩影。因此,这个作品只能拿我们党在土改中的政策去衡量。离开了这个标准,我以为很难涉及到这篇小说的本质。”
赵树理应该同意耿西对《邪不压正》的判断,他在回应这场讨论的《关于〈邪不压正〉》一文中特别强调:“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,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身上,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,故对小昌、小旦和聚财写的比较突出一点”,与这种构想有关,“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,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,在主观上我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”,他俩的恋爱关系不过是条结构上的“绳子”而已,“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,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”。由此一来,《邪不压正》中的人物“刘锡元父子、聚财、二姨、锡恩、小四、安发、老拐、小昌、小旦等人,或详或略,我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”,这样才能“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(土改中的干部群众),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,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”。
如果着眼于“事”,《邪不压正》的重点不在“恋爱”,而在“土改”,这点恐怕相当清楚;然而着眼于“人”,《邪不压正》究竟塑造出了怎样的主要人物形象,是聚财还是软英?就不太明白了。与赵树理的《关于〈邪不压正〉》同时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,还有一篇竹可羽的《评〈邪不压正〉和〈传家宝〉》,这篇评论同样具有总结这场讨论的性质:“这篇小说的主题,既非软英和小宝的恋爱故事(党自强说),也非党的中农政策问题(耿西说);这篇小说的主人公,既非软英和小宝(党自强说),也非元孩和聚财(耿西说),而是软英和聚财”。 很显然,竹可羽试图整合两种互相冲突的说法,同时也指出赵树理的这篇小说“问题就在于作者把正面的主要的人物,把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忽略了”,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就在于赵树理没有塑造好“软英”这个“主要正面人物”:“作者把软英写成一个等待着问题解决的消极人物,作者没有把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,指出合理的争取或斗争过程。因此,这个问题这个人物,没有给与我们读者以应有的教育意义”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竹可羽对赵树理的批评,并非完全着眼于“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”,他读了赵树理的《关于〈邪不压正〉》后,又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《再谈谈〈关于《邪不压正》〉》,进一步联系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的创作方法,以俄苏文学的果戈里《死魂灵》和高尔基《母亲》塑造“典型人物”为创作典范,认为“人物创造”,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“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”,“因此,假使这可以算是作者创作思想上不够的地方,那末,这个弱点正好在《邪不压正》上明显地暴露出来,并在《关于〈邪不压正〉》上作了这个弱点的一种说明”。进而告诫赵树理,在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文学中,“人的因素”具有“决定的意义”,“因为人,永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,永远是一个故事、事件、或问题的主题。所以说,社会主义现实主义,首先在善于描写人。但,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,似乎还没有普遍被重视起来……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,似乎也还没有这样自觉地重视这个问题”。
确实,赵树理的创作并不以“人”为中心,也很难说他塑造出了什么令人难忘的“典型形象”。就像赵树理自己所说的那样,“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”,写作的材料“大部分是是拾来的,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,想不拾也躲不开”。 这种似乎比较被动的创作方法,正是被竹可羽视为对“人物创造”还处于“一种自在状态”的表现。采访并翻译过赵树理三部书的杰克•贝尔登同样对他小说中的“人物描写”表示失望:“…人物往往只有个名字,只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典型,什么个性也没表现出来,没有一个作为有思想的人来充分展开的人物。” 无论是认为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够“典型”(如竹可羽),还是缺乏“个性”(贝尔登),都意味着赵树理小说不以“人”为重点和中心的写法,和一般意义上的“现代小说”有较大的分野,也使得深受“现代小说”阅读趣味影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难以理解赵树理的小说。
但对于试图冲破“现代小说”乃至“现代主体”惯例的文学研究者,赵树理小说的这一“反现代”的特质却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洲之内彻在讨论“赵树理文学的特色”时,非常具体地指出“赵树理小说”与以“心理主义”为基本特征的“现代小说”的区别:“赵树理的小说没有人物分析。既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,同时又是消弱现代小说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,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的。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近了死胡同。即使这样,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,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,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。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,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。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等。对于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。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,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即: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,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。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!” 而竹内好则更近一步地确认了“赵树理文学”这种“反现代”的“现代”特质:“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,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、杂乱无章的和浑沌不清的东西,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。因此,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,即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?…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,似乎觉得有些粗糙。然而,如果仔细咀嚼,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。稍加夸张的话,可以说起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,删一字嫌少的程度。在作者和读者没有分化的中世纪文学中,任何杰作都未曾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。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,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,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超脱出来这一点。赵树理文学之新颖,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,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。”
赵树理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说具有“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”、“重返现代”的特质,但竹内好指出他的作品“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,删一字嫌少的程度”,赵树理想必会很满意。赵树理小说的结构不以“人”为焦点,而是以“事”为重心,看似随意,却极用心。只不过这份“用心”不一定能被那些一直要求小说写“人”的读者充分体会罢了。按照赵树理的说法,他的小说重点在“事”,却也不是为“写事”而“写事”,“事”的背后是“问题”:“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,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,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”。 这段话常被简单地理解为“赵树理小说”就是“问题小说”,然而,如果把“问题”放在之前讨论的赵树理小说的焦点从“人”到“事”的转换中,就会发现“问题小说”也不简单。“事”一旦遇到“问题”,就从静态的存在变成动态的过程,就意味着原来的存在遭到质疑,过去的秩序不再稳定。因此,人们可以藉由这一时刻,追问这“事”合不合“道理”?通不通“情理”?赵树理通过“问题”,把“事”、“理”、“情”三者勾连起来,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系,让“事”不断地处于“大道理”和“小道理”、“新道理”和“旧道理”以及“人情”、“爱情”、“阶级情”等不断冲突、更新与融合的过程中:譬如乡村男女过去的婚姻都是“媒妁之言,父母之命”,但“婚姻法”颁布了,小青年的“爱情”就不仅“合情”,而且“合理”、“合法”了(《小二黑结婚》;阎家山一直是富人掌权、穷人受压,但共产党来了,这样的“事”就不合“理”了(《李有才板话》);地主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从来不算是“剥削”,但如今是“劳动”还是“土地”创造“价值”,这“理”一定要辩辩清楚了(《地板》)……由于围绕“问题”来组织“事”、“理”、“情”之间的关系,不只使得赵树理小说“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,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”,并且也让作品的“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,删一字嫌少的程度”。这种既将“内容”形式化,又把“形式”内容化的方式是“赵树理文学”的真正“新颖”之处,其关注的核心并非日本学者所感兴趣的“现代主体”之批判意识,而是新的“道理”是否能够合符“情理”地深刻改变、契合并升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种种“事情”。至于“人”,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抽象的“人性”和“主体”,只有回到“事情”及其遭遇“问题”的过程中,“人”的改变才变得合“情”合“理”。如此看来,《邪不压正》中聚财那一句“这真是个说理地方”,对“赵树理文学”来说,可谓画龙点睛之笔。


 会员登录
会员登录





